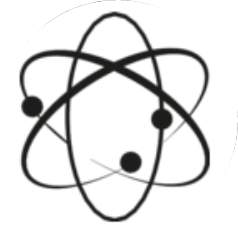论述20世纪50年代“颂歌”给诗坛带来的新诗风和存在的缺失。
天安门城楼上五星红旗的升起,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。摆脱了深重苦难的人民群众,满怀喜悦地赞美新生活,歌颂党和领袖,欢声笑语响彻神州。这一时代的“兴奋点”,必然使敏感的诗人们适时地调整创作视角,尽兴地喷发心中激情。于是,一首首昂扬欢快的“颂歌”,便构成了1949年以后初期诗坛的主旋律。曾经预言古老中国必将像火中凤凰一样获得新生的郭沫若,以一曲格调高亢、情绪豪迈的《新华颂》率先揭开颂歌诗潮的序幕,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。暗夜里曾向渴望光明的人们传递过“黎明的通知”的艾青,面对新时代的晴空艳阳,高唱起《我想念我的祖国》。何其芳抚今追昔、百感交集地欢呼《我们最伟大的节日》,臧克家分外深切地感受到《祖国在前进》。此外,冯至的《我的感谢》、朱子奇的《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》、石方禹的《和平最强音》、王莘的《歌唱祖国》等,也都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诗作。颂歌主潮无疑给诗坛带来了明朗的色调和昂扬的诗风,但与此同时,诗歌创作中若干不应忽视的缺失亦逐渐暴露了出来。其主要表现为:题材不够多样,形式比较单一;简单配合政治运动、中心工作的“传声筒”倾向已在部分诗作中初露端倪;以赞颂新时代、新生活为己任的诗人们,大抵致力于外部现实图景的描绘而回避“自我”形象的抒写;对人的精神世界、情感世界作深入揭示的诗篇更是凤毛麟角。凡此种种,均导致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的诗坛未能摆脱“大一统”的创作格局,而作品艺术风格的趋同,诗人艺术个性的萎缩,都是不利于诗歌的健康发展的。